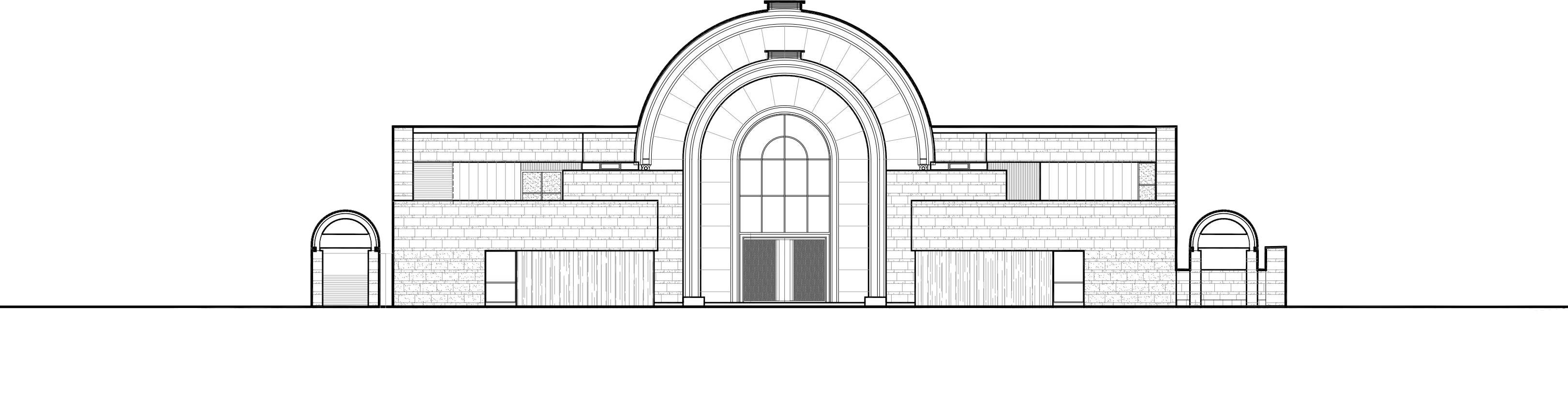我的母亲——吴洪起
邱伯兰
吴洪起是我的母亲,生于一八九四年枣庄市南园村一个贫苦菜农家庭。
一九一三年,我母亲十九岁出嫁。
我父东邱焕文,也是个没地没产的穷汉。祖籍胶东。祖父曾参加过捻军反清起义。后流落原峄县陈家湖安家。
一九〇七年,父亲十六岁随祖父逃荒到苏北,为生活所迫,入江苏陆军第二十三协当新军。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回到峄县齐村定居。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父亲又要扛枪,到贾汪当了警兵。一九一九年他受“五·四”爱国运动影响,登台演讲,反对“二十一条”,排斥日货,被矿警队长责打四十军棍,开除回家。
一九二一年,父来逃到关外,投入张作霖部。六年间,从大兵升至少校团长,率队驻苏鲁边。在奉军期间,响应北伐军革命,和孙伯英叔权毅然率队起义,将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苏鲁游击队,这支部队后被蒋介石缴了械。
一九三一年春,父亲在徐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四十岁,母亲三十七岁。
这年春天,杨树刚鼓芽,父亲从徐州领来两位“客人”。
我母亲奇怪的是这两个面带雅气的比我父亲小十几岁的年青人竟受到他那样的尊敬。
年青人都仪表端正,衣帽整洁,热情大方。特别是那个较年轻的,戴金丝眼镜说满口南方话的,开口就打趣:
“嫂子!我们是来要饭的”!
“正好,我家刚买了二十亩地,就缺长工,看你敢不敢吃这碗饭。”
“长工!嫂子说对了,我俩就是来当长工的,二十亩太少了,再多的地我们也能种好。”
“客人”抱起我,问我会数多少数。还抢着拉风箱,说他没拉过。
母亲同他拉呱了:
“先生家是······”
“湖北阳新县。在江南,是蛮子,俗话说:“蛮不讲理,嫂子以后不能见怪。”
“江南是好地方,我到过苏州,那是鱼米之乡。”
“江南是鱼米之乡,但穷人是吃不上的,跟你们这里一样,靠地瓜、菜帮过日子,地瓜在我们那里叫红薯,庄户人过年时能吃上一碗年饭就不错了。”
“先生家也种地?”
“我能有那个家就好了。”他叹了口气:“我家是富户,谁知道有多少地,三里五里的都往我家送租,不怕嫂子见笑,小时上学,家里都让轿夫拾着。”
“你家那么好,怎么舍得让你出来?”
好个啥,我六年没回家了。都是人,有的坐轿、有的抬轿,这平等吗?!”
“说的也是。枣庄中兴公司请的德国老毛子不吃粮食,雇八个奶妈子喂他,不平等的事太多了。”
两个叔叔在我家住下了。后来才知道岁数大的是中共枣庄特委书记田位东,戴眼镜的是副书记郑乃序。
幼小无知的我,除了盼过年,就盼家里有客人。因这时家里就要添一两样菜,虽然不能上桌,也能拣些碗底。
一连几天,父亲的好友孙伯英叔叔(峄西工委书记)也领着王子刚叔叔(在我家宣誓入党的)来到我家,他俩也同父亲一样,非常尊重这两个年青人。每当他们聚集一块时,母亲就领着我到院子外,她纳鞋底,我看“小鸡”,就是看见陌生人走过来就大声“唤鸡”。
党的工作不可能让一个几岁的孩子知道这么多。
父亲告诉母亲,郑乃序是假名,他叫陈明道,家是财主,从小是奶妈、丫环伺候,后到省城读书,上了武汉大学。参加了共产党,他家每月给他十块大洋,他留两块搭伙,剩下八块全拿出来交给党作为活动经费。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北伐”杀共产党那会儿,要不是他未婚妻报信翻墙头逃走,险些送了这条命。
“他未婚妻呢?〞母亲急切地问。
“被国民党抓去杀了。”
“他到这儿来······”
“来做工的,过几天就下井拉大筐。”
“他是大学生,家又是财主,为什么要找罪受?”
“他为的是广大受苦人求解放。他下井拉大筐就能结识工人,成为工人的朋友,把工人组织起来,就能跟资本家斗,把白日旗换成红旗,将来就能把落介石打倒。”
“共产党都是这样为穷人吗?”
“不为穷人为自己,就不是共产党。”
“你怎么不参加?”
“我在徐州就参加了!”
“你是我也是!”
父亲笑了。母亲默认她自己是共产党。她相信自己的丈夫,也相信自己家里这些为党的事业进行活动的人们。
杨树放花,满眼青翠。小鸡撒欢的争饲嬉戏,大地沐浴在春晖的阳光里。母来领着我,拿着鞋底到院子大门口“看鸡。”
“嫂子:你进屋来!”
位东叔叔亲切地招呼着,我可高兴了。郑叔权口袋上褂着个小黑管管,能写出字来,我老是想玩玩、摸摸,可娘总是要领我去看“小鸡”。
“你消坐!”郑叔叔将钢笔递给我,特意将凳面擦擦。
娘笑开了:“啥事劳你的大驾,这么客气!”
“听话!挨着我。”
伯英叔是老熟人,闹惯了。
田叔叔端起一碗茶,送到娘手里:
“嫂子,这些天来,我们在这里又吃又住,看得出来,你是不烦的。你也知道,我们这几个人要干什么,这样大的危险,你心甘情愿和我们一样,我得谢谢你。”
娘察觉父亲的几个“兄弟”有话要对他说,就随手从屋角拉出了一个小马凳。
“嫂子,”位东叔叔又把话接过去了。
“你知道了,我们这几个都是共产党。共产党只能为老百姓办事,不能顾家,今后……”
母亲误解了,说:“你们放心,我向来不管他的事,不怕你们笑话,我十九岁跟他,又一个十九过来了,他在家过了几天?就只因为穷,到关外,下江南,一辈子当兵就跟枪亲,喜欢闹革命。如今这样为穷人办事,我没有说的。、”
叔叔们都乐了。郑叔告诉她,共产党枣庄特委已经成立,田位东是书记,党委机关就设在我家,党的任务就是要把枣庄建成红色苏区,把抱犊崮山区建成红色根据地。
“真有那一天,死也甘心!”
田叔接过话说:“斗争是不怕死的。我一个人到街上,说自己是共产党,那早就被抓去杀了。依靠你们几个,我就不怕有人抓我。我们都去找穷人,把枣庄的老百姓都联络起来,这就不是他抓我,到时候我要抓他。几千年的皇帝不是打倒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也一样能打倒。我们现在去联络人不能先说自己是共产党,说互济会,是大家伙帮助解决难 事的。这个互济会首先要掩护党员进出枣庄,今后经常会有党员来的,全国都有党。其次是要筹集款子,我们党现在没有钱,党员来往的路费、吃住都靠互济会设法。再一个就是要准备万一党员叫国民党抓去,互济会要花钱活动救人。国民党的警察、局长、县长,没一个不爱财的,要尽早花钱保出来。”
“互济会由我当不露面的主任,除了乃序,你们几位、嫂子你也是。对了,”他转向我父亲:“嫂子叫什么名哪?”
“哪有名!她爹娘没给她取名。”
“那我们党来给她取个名好了!”乃序叔接过话,“枣庄有了党,枣庄要建成苏区,枣庄要飘扬红旗,红旗是我们的希望,嫂子就叫“洪起”吧!”
从此,母亲有了名字——吴洪起!
不久,田叔,郑叔由父亲介绍到枣庄中兴公司齐家柜下井干了工。孙伯英叔叔和王子刚叔叔到峄西一带搞农村工作,党在鲁南的活动开展起来了。这时中共山东省委军事委员会的程寄平,和济南来搞学生运动的朱同云,还有姓赵的、姓魏的叔叔都常来我家。
我父亲有一张遗稿中记有:“也有上海中央来检查工作的。有一个驼背四川的同志,说姓张,来枣庄检查工作。据讲中央在上海,周恩来同志领导的。”
这些来的叔叔都在我家找田叔、郑叔接头,母亲对每个党派来工作的同志,都象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安排吃住,洗补衣服,她对这些叔叔说:“我家就是你们的家!”
田叔、郑叔往往从井下带着满身劳累和遍体炭污回到家来,尤其是郑叔,近视眼,下井他不戴眼镜,到处碰的青一块,紫一块,母亲见他俩回来又高兴,又心疼。
矿区的工人在田位东、郑乃序两位叔叔亲自启发和组织下,提高了觉悟,加强了斗志,坚信自己能够团结起来,敢于斗争就能胜利。
我父亲另一纸遗稿中,有这样几句记录:“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春天,枣庄特委统计发展了党员十三人,有积极群众二十多人,建立了老枣庄、金家庄、大洼、田家庄、雷家村、石碑、车站、佟家楼、尤家村、窑神庙、陈家庄,后龙头、南马道十三处的通讯联络站”。
娘常领着我到枣庄去“赶集”,行前总是要在发髻或裹脚布里藏上一张字条,有时回来也带回小纸条,父亲用水一浸,字就出来了。
枣庄不大、中兴公司却不小,它的董事长是两个赫赫有名的大总统黎元洪和徐世昌,经理是黎总统的儿子黎绍基。
这些大总统,大军阀为何对咱这鲁南小镇——枣庄有如此情感?其原因就是这里有煤,他们开公司,出煤炭,发大财。眷养了一支近千人的矿警队护矿,特委的目的是想夺取这支武装队伍的武器、拉起工人队伍,到抱犊崮山区建立红色根据地。
母亲对进山充满信心。为了党进山活动有经费、生活有着落,她将我家的二十亩地卖了二百大洋。她为我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叮嘱我要紧跟大人跑,千万不能丢了。
娘见我眼泪汪汪,舍不得走,搂住我说:“闺女,咱家隔壁崔家的地主打骂丫环、逼死长工你都见了、穷人多苦,穷人的苦是地主造成的,为了不受穷,农民佃户就要和地主斗争,下窑的工人就应和中兴公司的资本家斗争。郑叔家里是有钱人家,不在家享福几千里来咱枣庄下煤窑、拉大筐,不就是要帮穷人翻身,咱进山过人人都一样的日子不好吗?”
我似懂非懂,不再难过,询问起山里有粮吗?有核桃、梨、柿子、山楂吗?野花多吗?
田位东叔叔、郑乃序叔叔因叛徒佟振江、孟广银的出卖,先后被国民党逮捕了,押到峄县城监狱。母亲非常着急,收拾了两双新布鞋、几件衣服和十块银元,要我叔伯哥哥邱伯溪到峰县监狱看望,伯溪哥说:“五婶您好糊涂,县府这次办的是共产党大案,田、郑都咬定同任何人没有关系,人家正找不着咱,咱这一送钱不就找着了。”母亲急得直掉泪。
没过多久,二位叔叔在济南千佛山下英勇就义的消息传到我家。母亲再也控制不住,放声大哭。
田、郑遇难,枣庄特委同上级党的关系完全断了。我父母都牢记郑乃序叔叔临别前说的:“党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父母将手头原准备进山的一笔钱拿出来,到枣庄街里开药铺,以造成能接近党的机会(我家原住齐村,离枣庄六里)。
一九三二年秋,南马道一座两层的砖质楼房挂上了“同顺兴中药店”的招牌、时隔不久,老街也有一家“同春堂药店”开张。药店在鸡市口的一间草棚,货只有几把草药,几只缸,但名气出来了,管事的庞先生妙手回春,药到病除。
母亲装着赶集,到鸡市口侦察了两次,回来对父亲说:“生意倒不错,进出都是穷人,像满高兴似的。我见庞先生送看病的出来,挺和气。那模样比你小几岁,也留着短胡,你自己去啦啦吧,反正不会是坏人。”
父亲随后去了几趟,把庞先生领到我家、“庞沛霖”是郭子化的化名。郭叔叔对我家经营的“同顺兴药店”非常满意。这幢两层砖质楼房,它在五十年前的枣庄是小有气派,非常便于同志们往来住宿。是理想的党的地下机关。
一九三三年“五一”罢工胜利后,矿区党委在“同顺兴药店”的楼上正式成立。党委决定“同顺兴”改名为“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
我家有“中药”有“西药”,什么人都可以来往。有“运”有“销”,什么人都可以居住。
“合作社”挂招牌那天,鞭炮响着。
人们议论着:邱家发了,生意真好!
是“发”了。你看一天到晚看“病”的,抓“药”的,送“货”的川流不息,白天开 “洋匣子” 听戏文,晚上点“自亮灯”。
丛林(他让我喊他大哥)首先从沛县调来枣庄,以后郭致远叔叔也来了,他们比我哥哥大几岁,都是党的主要工作人员。“合作社”经常住的满满的。
粉碎“四人帮”后,郭致远叔叔到泰安干部疗养院看我母亲,母来做了饭,致远叔端起碗说:“老嫂子,四十多年前,您就给我做饭,今天我要多吃一碗!”
是的,三十年代我母亲就是边区党委地下机关的炊事员和通讯员,她天天要烙饼,顿顿要烧汤,夜夜要洗衣服,难得有闲着的时候,活,是那样的劳累,而她干得却是那样高兴。
“七、七”事变,华北沦陷,祖国的半壁河山已在日本强盗的铁蹄之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侯,何一萍叔叔来到我家,这时边区特委和郭子化叔叔已迁徐州,枣庄设立了鲁南中心县委,一萍叔是特委委员兼中心县委书记,机关仍在我家的“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
日寇逼近,蒋介石的国民党被迫宣布:“抗战”,对付共产党人的屠刀稍有收敛。何一萍叔叔具体领导枣庄及鲁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我当时上小学三年级,学校停了课,小学生也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我参加儿童团,学习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和《长城沦》。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枣庄抗敌后援会主持召开了四万人的誓师大会,韩文一叔叔上台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揭露了国民党不抵抗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母亲拉着我就在人群中,她没有激动地呼口号,也没有冲上台去讲几句话,她站在那里,成了泪人。
一九三八年八月,我们随抗日义勇队东征,到达四县边联的高桥、大炉根据地。
我们进了山,父亲到义勇队工作去了。母亲带着哥哥伯达和我来到徐庄。开了一家药店作为党的联络点,母亲在药铺生活多年,对中草药也稍有认识。哥哥伯达开始参加了党的工作。日本人进不了山,飞机到处狂轰滥炸,一天对徐庄轰炸好几次,有一次炸弹投到我们药铺,三口人都被土墙埋住了,是人家扒开砖土救出来的。
枣庄的家被日寇占领了,徐庄的家被日本飞机炸塌了。
日本强盗的暴行,“中央军”的溃逃和抢劫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怒火,不久,哥哥也离开我们,直接到抗战的第一线。进山后,所制的中药大部在多次迁移中损失,少部份由我母亲携带以卖药作职业掩护之用。原药品合作社的股金属一般社员的都在撤退前还给了社员,剩余的部份大部为张毓昆先生的投资,其余一部分属我家的资金。当父亲和母亲商量将西药工具和器械交义勇队时母亲也极表同意。父亲还说张家的资金目前不能偿还了,只好等抗日战争胜利了用抗战的胜利来还良心账吧!母亲领着我,背起药箱,裹紧小脚,踏遍了抱犊崮的山山水水,一边搜集敌伪活动情报,以便选医送药到山村,她是菜农出身,农活在行,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一边干一边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发动组织妇救会。抗战时期,抱犊崮的群众,大多数都知道“邱大娘”。
一天,父亲回到我和母亲临时居住的外峪子村,问我是参加抗战还是跟在母亲身边?这个不算突然的问题,突然提出来,我为难起来,真舍不得离开母亲。
早晨起来,娘替我梳头。心情有些激动,叮咛我要记住田叔叔、郑叔叔。
一滴泪水就滴在我的脖子上,我也哭了。
起程路上,娘叮嘱我不要想家。
“只有打倒了日本鬼子,我们才能在一起”。
离外峪子已有几里地了,娘停下来,那颤抖的手再次为我理理头发:“跟着你爹,一直朝前走,别回头。”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三周岁的我,按照母亲的嘱咐,跟着父亲,奔向抗日救亡的战斗行列,成了鲁南军区宣传队的一名战士。
“一直朝前走,别回头”。这是母亲送我走进革命大家庭的赠言,也成了我终身的座右铭。
有的材料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我母亲于一九四一年,四、二五事变,国民党进攻,鬼子扫荡,积蓄五块钱,拿出买米做饭,支持党员侦察敌人,打了胜仗。
国民党却乘春荒之际侵入我根据地,边区县被压缩到一枪能打透的“一线牵”的狭长地带。母亲同刘清如,葛成俊、荆守胜等同志一起,坚持在这里。
鲁南事变时,我随军区主力较移到邹县地区十八趟。离开根据地后,给养更困难了,我们宣传队只有摘野果,喝沟水来解决饥渴。很快,严重的疾病流传开来,不少“小鬼”都身躺山坡,再也起不来了。我也病得很重,却不知是怎样活过来的。
在这段时间里,母亲也听不到父亲、哥哥的消息,时刻惦念着。还听人传说,我们军区宣传队的孩子们,在过敌人封锁时,均被敌人机枪打死了。她心如刀绞,天天流泪,盼望能听到准确消息。
半年后,我随主力部队又回到抱犊崮根据地。娘听说宣传队回来了,早就等在我们行军途中的路口,当她从“小鬼”的队伍里认出我来时,一把抱住了我,痛哭起来。
虽然回到老根据地,困难还是相当大,供给也很差,娘经常翻山越岭,追赶我们军区宣传队的驻地,给我们这些“小鬼”带点煎饼,窝窝头,老咸菜。一段时期,宣传队盼望着“邱大娘”。他(她)们是战士,也是“小鬼”。
我母亲的《登记表》在奖励与处分栏里填有她一九四九年在峄县山阴鲁南第五区医院为给病伤员洗血衣受大会表扬,口头奖励的记载。
乍一看,我几乎怔住了。一无奖品,二无奖状,这算奖励吗?!
随着这行记录文字,我的思绪回到一九四九年,我在滋阳县工作,父亲派人牵来一匹马,接我到鲁南医院驻地去看娘,她周身疼痛,在床上打滚。她的病,有相当长的历史了。
记得抗日后期,我沂蒙山根据地得以巩固,地方政权相继建立,地下活动的情报联络工作已不需要,一九四三年,年近半百的母亲来到梁邱鲁南军区后方医院,她挑选了为病伤员洗衣服,洗敷料的工作。衣被的污垢,敷料的血迹, 用她那一双冻得跟萝卜一样的手指在水沟中搓洗。她洗到日本鬼子投了降。洗到蒋介石飞到台湾。她待伤病员如亲生子女,她周身疼痛,却心甘情愿。
母亲病好了,她铭记这“大会表扬,口头奖励。”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
有一天,母亲脸上明显留有愠色,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入党了吗?”娘问我了。
“入党五年了。”
“你五年了,我还不是呢!跟着党跑了十六个年头,我的名都是党给取的。白色恐怖时,地下党那么秘密都不避回 我,如今有半个天下,公开了,开会不叫我参加,说我不是党员,这不……。”
我也不相信,用眼光问父亲。
父亲早就在笑:“你问伯兰,谁入党不得自己要求自己申请,得有党员介绍,得向党宣暂,你一样都没办过,非说我是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我要是国民党你也当国民党?”
“你不够国民党那块料!”
她自己缓和了气氛:“共产党好也好在这里,一点面子都不讲。这十六年,什么大干部我没见过,一家人都早入党了,剩我自己也非按规定办事,按规定办就按规定办!”
不久,母亲写了入党申请,在李韶九、孙怡然两同志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星红旗升起来了,母亲万分高兴,多年夙愿终于实现。她同父亲都调到滕县专署医院,仍然挑选了洗衣这份工作,在登记表的职务栏,她让人填上 “工人”两个字。
建国后,干部的待遇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母亲高兴极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还能拿薪金。评级会上,她问:“最高是哪个级?”
“最低呢?”
“那我要二十六。快六十岁了,要那些钱干什么?我要二十六级。”
医院的污物桶里,每天都有很多绷带、敷料,母亲看见心疼,她都捡出来,洗净血污再煮沸消毒,下次再用。结果,她感染了。完全丧失活动能力,瘫痪了两年,农民出身的母亲体质好,经治疗后能下床了,但已不能胜任“洗衣工”这个职务了。
一九五八年,六十五岁的母亲同六十八岁的父亲同时在北京退休。
父母喜欢中华民族的象征——泰山。经自己要求,有关方面联系,他们迁到泰安定居。
一九六九年,我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离京去湖北途中绕道泰安,母亲对我说:
“前些时,北京来了两个臂带红袖章,穿黄制服的人,由管理员领着来找我。我一听北京来的,准是你郭叔惦记着我,派人来看看,连忙招呼打听起来,可这两个人说是姓“吴”(无)的司令部派来的,是调查郭子化叛变投敌的历史材料,还要我同你郭叔划清界线。我一听就火了,也顾不得讲客气,我说:“叛徒!你俩见过吗?当时还没出生吧。”我七十五了,怕他怎的,我说我见过叛徒,一个三八年叫我们抓住了,老头要用枪打,是我叫用刀砍的。另一个佟振江解放后抓住,也是我老头写材料定的死罪。这两个叛徒害死了田位东、郑乃序。郭子化叛变害了谁?!这两个人说是调查一九三六年端午节的头几天,郭子化被一个姓米的叛徒逮走的事。我说:
“这事我知道,是李韶九和我老头几个人商量保出来的,出来后就跑到山里,以后拉起队伍打游击,是叛徒还要我们保!!还要跑!!”这两个人还没个完。
我见他们胸前的像章就问:“你俩戴谁的像章?”他说:“是毛主席的。”我说:“不对,不是毛主席,休养所给我送来的毛主席都有领章、帽徽。”他说:“这是什么时侯,是军阀统治时期,去安源还没上井岗山呢,哪来的领章帽徽?”这可叫我有话说了:“你刚才不讲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条件?毛主席这时为什么不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呢?后生,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去问问你的祖辈吧。”
两个人没话说了,也没叫我按手印,走了。我连夜赶到兖州,找你哥哥伯达——他还在靠边站,时刻准备挨斗,我叫他只说一句话:“什么也不知道。”
我在干校“毕业”回家前,提前给母亲写了一封信,问她需要什么?
回信开的单子是小电灯泡两个,长钉十枚,火柴一包。
回到泰安,我拆开一包“孝感麻糖”递一片到她嘴里,娘说好吃。当她知道是一元多一盒时又不高兴了。说我乱花钱。
母亲晚年有旧的习俗思想,安排死后与父亲合葬,要我嫂子为她准备了一口棺材,我们动员她发扬老一㹃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质,带头移风易俗,不用棺材,实行火葬。因刚实行火葬,还有阻力。母亲开始有些犹豫,后来还是同意了。说党员就要听党的安排,立即把棺材处理掉。
泰安地委高书记常去探望邱大娘,知道了我母亲是二十六级的“干部休养员”,在三中全会后,他和地委组织部商量,同北京中医研究院——母亲原工作单位取得联系。一九八〇年八月,地委组织部以中央有关规定和负责同志讲话精神,决定将我母亲由行政二十六级改为十七级。
这时,八十六岁的母亲已经住进泰安人民医院。
我从北京赶去泰安时,母亲已病危。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日母亲就逝世了。
对后事的安排,母来临终告诫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谢绝任何亲友送花圈,要将骨灰同父亲合葬在一起。
泰安县老干部办公室发出吴洪起同志逝世的《讣告》中提到:“吴洪起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孙赞勋整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北京
编者注:
邱伯兰,女,一九二七年二月出生。山东省枣庄市齐村人。一九四〇年八月参加鲁南军区宣传队,一九四二年九月入党。历任宣传员、教师、费县县委文书、鲁南四地委股长、平邑县团工委、副书记;历任峄县团工委副书记、陶庄煤矿团总支书记、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枣庄矿务局组织部副部长,阜新煤矿学院组织部部长。一九六五年调北京,一九七二年调故宫工作,现已离休,住北京。
原文刊登于《枣庄地区党史资料(第四辑)》,中共枣庄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1986年8月)